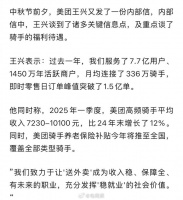不妥协、不跟风,MIT中国学者发现兼具磁性、手性、超导性的新量子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路飞
自1911年首次观察到超导体以来,物理学家假设所有超导材料都应该同时表现出零电阻和与磁性的排斥。然而,5月22日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的巨龙在Nature封面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一种在五层菱面体堆叠石墨烯中同时存在磁性(自旋磁性)、手性(轨道磁性)和超导性的新量子态。这一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于超导性和磁性的传统认知,为理解和开发量子材料提供了全新视角。
撰文|路飞
今年5月22日,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的巨龙与合作者在Nature杂志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一种在五层菱面体堆叠石墨烯中同时存在磁性、手性和超导性的新的量子态。“这项研究成果无论是对我们研究小组,还是对凝聚态物理学界来说,都是振奋人心的。”接受《返朴》采访时,巨龙说道。
巨龙现为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是一名凝聚态物理学家。在此之前,他的研究小组于2023年在菱方石墨烯和六方氮化硼的摩尔超晶格中发现了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发现是在没有理论预言的情况下做出的,令凝聚态物理学界颇感意外。2024年,在进一步探索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机理时,他们发现了在摩尔超晶格效应缺失的情况下,菱方石墨烯表现出了手性超导的性质。
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巨龙一开始研究菱方晶体石墨烯的动机在于探索受量子力学原理支配的强关联电子材料的特性,而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具体现象。“当大量的原子和电子以晶体形式聚集在一起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怎样的宏观现象,这非常令人着迷。”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手性超导体,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的强关联电子现象,在没有理论预言的情况下,被巨龙的研究小组在菱方晶体石墨烯中先后发现。
迷人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要了解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还要从霍尔效应说起。
1879年,美国科学家埃德温·霍尔(Edwin Hall)在探究金属导电机制时观察到:当对一块导体施加电流,并同时施加一个与电流方向垂直的磁场时,由于洛伦兹力的作用,导体内电子的运动轨迹会发生偏转,进而在垂直于电流和磁场方向的导体两端产生电压,该电压被称作霍尔电压,这一现象则被命名为霍尔效应。
1980年初,德国物理学家K.von Klitzing在研究二维电子系统的霍尔电阻时,于1.5 K低温(宇宙背景温度约为2.7 K)和18 T强磁场(强度约为地磁场的几十万倍)的极端条件下发现,样品的霍尔电阻出现了一系列量子化的平台,同时纵向电阻呈现零电阻态。包括Klitzing在内的众多科学家迅速意识到,这一现象与二维电子系统在磁场中形成的朗道能级相关,且量子化霍尔平台恰好出现在朗道能级填充为整数的情况下,因此该现象被称为整数量子霍尔效应。鉴于这一重大实验发现,Klitzing于1985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2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崔琦与H.Stormer,采用纯度更高的砷化镓量子阱二维电子样品,并在更低温环境下开展研究,成功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这一更为惊人的现象。他们观察到,当朗道能级填充因子为分数时,同样会出现量子化的霍尔平台,这一现象表明系统中产生了分数电荷激发。要知道,单个电子携带一份元电荷,在真空中电子不会出现分数电荷,然而当大量电子在固体材料中发生复杂相互作用,就能够衍生出分数电荷激发。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是一种与整数量子霍尔效应有着本质区别的强关联量子物态,属于奇异的量子流体。它具备由电子关联形成的拓扑序,展现出长程量子纠缠与分数电荷激发的特性,部分分数量子霍尔态的准粒子激发甚至可能遵循非阿贝尔统计,因而成为拓扑量子计算的重要备选方案之一。凭借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与理论阐释,相关研究成果荣获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整数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出现,均离不开磁场下二维电子系统所形成的朗道能级结构,而这一结构的产生依赖强磁场与极低温条件。由此引出疑问:是否存在无需磁场的量子霍尔效应?1988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D.Haldane率先给出解答。他设想为石墨烯赋予一种特殊的磁通结构,以此达成净磁场为零的状态。经计算,他证实在此情形下能够出现零磁场下的整数量子霍尔效应,该效应后来被命名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项理论成果也是D.Haldane荣获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关键成就之一。
Haldane模型要求的磁通结构在真实材料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之后20余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未能获得实验实现。直到2013年,中国科学家薛其坤院士带领的实验团队,于磁性掺杂的拓扑绝缘体薄膜中,首次观测到整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重大科研成果,也荣获了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那么,是否能够在零磁场条件下实现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呢?长久以来,人们始终未能找到可实现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材料体系,直到二维材料莫尔超晶格的问世,才为这一难题带来了新的突破契机。
自然界中存在一类具有天然层状结构的材料,其层间通过相对较弱的范德华力(分子或原子之间存在的微弱的非键合相互作用力)连接,因此这类材料易于解理,如今通常简称为二维材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层状材料当属石墨——2004年,英国科学家A.Geim与K.Novoselov通过胶带剥离石墨的方法,首次成功制备出单原子层的石墨烯。
石墨烯本身具备诸多有趣的物理特性,而更引人关注的是,当将两层石墨烯堆叠并旋转特定角度(即后来所称的“魔角”)时,会形成新的周期性结构——摩尔超晶格。这种超晶格能显著改变材料的能带结构与物理性质,使得魔角石墨烯呈现出单层石墨烯所不具备的诸多特性。例如,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P.Jarillo-Herrero团队首次在魔角石墨烯中观测到超导态和关联绝缘体,这一发现掀起了利用摩尔超晶格研究二维材料新奇物性的热潮。
基于二维材料摩尔超晶格体系,国内外研究者围绕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展开了大量理论探索,最终将研究重点聚焦于转角MoTe₂和转角石墨烯体系(通过人工精确旋转两层晶体构建摩尔超晶格)。实验上,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于2023年8月在转角MoTe₂中首次被发现。
至此,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研究的大体脉络梳理完毕,本文的主角登场了。
这和任何一种超导体都不一样
巨龙自从读博时开始,一直在研究石墨烯的电子特性,从一层、二层、三层、四层直到五层石墨烯。通过简单的计算,他发现四层和五层的电子能带明显要比三层以下更平,有利于催生由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奇异现象。直到2023年夏天,巨龙带领团队通过实验发现,如果将五层结构石墨烯与六方氮化硼(hBN)对齐,就会出现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不同于转角MoTe₂,这一发现是在完全没有理论预测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且当时就观测到了6个不同的分数态(远多于转角MoTe₂中的两个)。
这一发现当时在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一是这项研究证明了基于菱方晶体石墨烯的摩尔超晶格可以产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而不是大家之前预言的转角石墨烯。二来前者产生此效应的微观机理明显有悖于常理,也明显不同于转角MoTe₂。直到现在,理论学家依然没有在这一机理上达成一致意见。有些理论建议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甚至不需要摩尔超晶格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究微观机理,巨龙团队故意将石墨烯和氮化硼之间的转角增大,以弱化摩尔效应直至可以忽略。让团队成员震惊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超导性。
按照凝聚态物理的研究范式,巨龙想更进一步了解这种新的超导体将如何响应外部磁场。于是在材料上施加了磁场和电流,并测量了材料的电阻。当他们将磁场从负调到正并再次调回来时,他们观察到材料先是保持其超导、零电阻状态,然后电阻短暂地飙升,最后后切换回零,并返回到超导状态。当反向调节磁场时,电阻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而且电阻对正反向磁场的响应表现出像磁铁一样的磁滞回现象。简单来说,超导和磁性(非自旋磁性,而是轨道磁性,证明了超导具有手性)在同一个材料的同一种状态里共存了。不仅如此,电阻的磁滞回线现象在超导转变温度以上也被观测到了。
这个发现非常不寻常,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种超导体表现出这样的磁滞洄现象。毕竟自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卡麦林·昂尼斯(Heike Kamerlingh Onnes)首次观察到超导体以来,超导研究的基本经验是超导性和磁性应该是互相排斥的。
“我不是做超导出身的,当看到这个现象时我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地去向很多研究超导体的专家请教,他们都没有发现过这个现象,更别说是在平平无奇的晶体石墨烯中,没有施加魔角石墨烯那样的层间转角或者其他的复杂的实验条件!”巨龙回忆道。
以往石墨烯的研究围绕在魔角石墨烯的超导性上,即把石墨烯的层间转角偏转到某个精确角度使其成为超导体;也有研究晶体石墨烯的磁性,例如通过调整纳米带的宽度、边缘结构或者掺杂非碳原子调节石墨烯磁性,或者通过实现电子平带来引发自旋和轨道磁矩。此时的实验结果摆在眼前,在晶体石墨烯中,超导和磁性共存了,这和此前任何一种超导体都不一样!
尽管这一发现似乎有悖常理,但团队接下来在六个类似的样本中均观察到了相同的现象。“我们推测菱方石墨烯的独特构型是关键。该材料具有非常简单的碳原子排列。由于其具有非常平坦的电子能带,电子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强烈。当冷却到超低温时,热涨落最小,这种量子相互作用可以导致电子配对和超导。不仅如此,在这个特殊的体系中,电子可以共同占据两个相反的动量状态或‘谷’之一。当所有电子都位于一个‘谷’中时,它们实际上会沿同一个方向旋转,而不是相反方向旋转。这种旋转类似于人的左手和右手,使得我们观测到的超导体具有了手性。当电子配对时,超导对总体上具有“非零”动量和轨道角动量,这种轨道旋转类似一个电流环,就可以产生轨道磁矩并被外加磁场翻转,导致我们观测到的磁滞回线现象。”
在以往的超导体(包括魔角和层数小于三层的晶体石墨烯)中,电子可以占据任一“谷”,任何一对电子通常由相互抵消的相反“谷”的电子组成。导致宏观上的超导体并不具备轨道磁矩和磁滞现象。
在理解所观测到的超导现象时,巨龙的理论合作者傅亮(MIT物理系教授)提供了关键的帮助,尤其是指出了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超导体在转变温度以上有电阻的磁滞洄现象。
说服大众接受新鲜事物总是困难重重,说服审稿专家更是一波三折。
这篇文章从2024年9月投稿,前后通过了三轮审稿。第一轮反馈中,一位审稿人态度积极,另外两位审稿人“完全没看懂”。巨龙团队不仅提交了纠正对方观念的解释说明,更进一步补充了更多的实验证据来支持手性超导的结论。第二轮反馈中,此前持反对意见的审稿人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能够把非常反对的人变成坚定支持的人”,这让团队喜出望外。第三轮反馈只剩下文章细枝末节的格式问题。
“如果我在标题中说明‘不需要魔角的一种石墨烯超导体’,编辑可能会找一些研究石墨烯相关的审稿人,文章接收速度会快一些。但是我们在文章里说的是‘手性超导体’,完全跳出了石墨烯或者二维超导体的范畴。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编辑可能会找一些和石墨烯完全不相关的审稿人,以跟所有超导体作比较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文章。这就会导致审稿人因为不熟悉石墨烯而误解我们的工作。”巨龙推测审稿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跟学生说,我们不应该牺牲这篇文章的价值,应该让所有研究超导体的人都知道这个工作。最终我们没有做出妥协。”
2025年5月22日,这篇文章在未经过编辑的情况下被Nature优先快速发表,在学界引起广泛轰动。
要做让人眼前一亮的研究
完成这项研究工作,可以说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是指巨龙在研究二维材料的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时候,误打误撞发现了五层菱面体石墨烯中同时存在磁性和超导性的新的量子态;必然性是指只有巨龙坚持用光学和电学手段研究别人眼中“平平无奇”的晶体石墨烯,哪怕遇到层层阻挠。
最大的拦路虎之一就是没有设备。这要追溯到2022年,巨龙一门心思在研究五层菱面体石墨烯,做出了石墨烯样品,但是苦于没有稀释制冷机设备。资金基本都去买光学设备了,只能去找别人合作借用稀释制冷机来做电学测量,但是碰一鼻子灰,因为机器不是说借用一次两次就可以了,有时候甚至要用几个月。很多人,包括系主任,劝他不要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研究,毕竟这是别人研究的舒适区,“我一个外人贸然闯进去风险太大,有可能影响到我在MIT拿终身教职。”巨龙说。
此外就是申请基金困难。“申请基金压力非常大,因为很难说服基金项目经理我可以比专门做电学实验的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域做出更好的工作。两年前到现在我还没有饿死,算是比较幸运的。”
但巨龙是一个冒险家,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一定要抓住。“所有这些外部压力反而让我觉得兴奋,因为一旦做出好的东西,每个人都会被震惊”。最终他东拼西凑,在2022年9月买了一台50万美元的稀释制冷机。
2023年6月稀释制冷机刚安装好,巨龙就带领学生紧锣密鼓开展了实验。一天下午,在办公室讨论时,研究生韩同航说“似乎看到了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哦’了一声,隔了几秒又和他确认,这一刻才意识到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结果!后面我们早上讨论下午做什么,下午讨论晚上做什么,节奏非常快,丝毫不知疲倦。”仅仅一年以后,在同一台稀释制冷机中他们又发现了手性超导体。
回看这些研究成果,本质上都在于避开主流,去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别人会觉得抛开非常火爆的魔角石墨烯而去研究少有人看好的晶体石墨烯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物理学的本质不在于体系本身的复杂性,而是在于在最简单的体系里发现最奇妙的现象。晶体石墨烯存在于天然石墨当中,具有最简单的结构和更好的均匀性。其本身就具有非常好的电子平带,并且可以被电场连续调节。这些好的性质是魔角石墨烯所不具备的。”
“纵观科学发展史,很多跳跃式发展就是需要有人不走寻常路。跟随别人的脚步做研究,确实是一条保守稳妥的路,但是这条路上人太拥挤了。我更想挑战现有的认知和知识框架,哪怕我可能会因此失去终身教职的机会。”
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手性超导的两篇文章对巨龙影响深远,可以说是“事业的转折点”,他不仅陆续收到了各大高校和国际会议的报告邀请,还能够和此前仰望的科研工作者并肩作战。“像文小刚老师,他是凝聚态物理学界的顶尖学者,我以前从未想到能和文老师有交集,如今研究课题有交叉,我和文老师会时不时一起交流研讨,并在手性超导的课题上(我)有幸一起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
菱形堆叠多层石墨烯展现出高可调性、低维度效应以及丰富的自旋和谷自由度,这些优势使其在拓扑超导、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巨龙表示,他们将进一步探索目前找到的这个超导体是否是拓扑超导体。“现有的理论都显示出这个超导体非常可能是拓扑的。”
“青年人还是要勇敢去探索新的领域,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巨龙说,在这两个实验中,研究生韩同航和博士后陆正光起到了关键作用。“跟我类似,他们两个之前也没有研究量子霍尔效应和超导的经验。这反而在最大程度保证了我们不被以往的经验所束缚,从而可以纯粹被好奇心驱使,来探索一个新的材料体系中所有可能的未被理论预言的新奇现象。”
作者简介
巨龙,1987年出生于山西太原,高中毕业于山西大学附中,曾获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银牌,2005年保送进入清华大学数理基础班学习,2009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2015年博士毕业后到康奈尔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19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至今,目前为MIT的Lawrence and Sarah W.Biedenharn Career Development副教授。
参考资料
[1]https://physics.mit.edu/faculty/long-ju/
[2]https://cqe.mit.edu/long-ju-2/
[3]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exotic-new-superconductors-delight-and-confound-20241206/
相关科普解读
神奇的手性超导:超导与磁性可以共存?
相关推荐
不妥协、不跟风,MIT中国学者发现兼具磁性、手性、超导性的新量子态
生命演化偏爱单一手性:为何蛋白质几乎都是“左撇子”?
「室温超导」,跨时代发现还是惊天诈骗?
寻找超导量子比特信息丢失的原因
笼目材料,凝聚态物理学家的团宠
几何密铺能解开生命手性之谜吗?
室温超导,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潮科技 | MIT开发水下压电传感器,兼具能量采集和“无线电”功能
MIT学者对话腾讯副总裁姚晓光:玩游戏这件事本身是有价值的
科学家们的百年超导之路
网址: 不妥协、不跟风,MIT中国学者发现兼具磁性、手性、超导性的新量子态 http://www.xishuta.com/newsview141598.html
推荐科技快讯

- 1问界商标转让释放信号:赛力斯 95792
- 2报告:抖音海外版下载量突破1 25736
- 3人类唯一的出路:变成人工智能 25175
- 4人类唯一的出路: 变成人工智 24611
- 5移动办公如何高效?谷歌研究了 24309
- 6华为 nova14深度评测: 13155
- 7滴滴出行被投诉价格操纵,网约 11888
- 82023年起,银行存取款迎来 10774
- 9五一来了,大数据杀熟又想来, 9794
- 10手机中存在一个监听开关,你关 9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