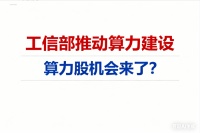412.15%的半导体订单增长,是否意味着微导纳米的ALD时代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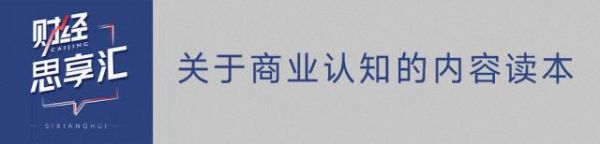
与 2022 年 1-9 月相比,微导纳米光伏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244.32%,半导体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412.15%
作者 | 洪雨晗 吴雨晴
编辑 | 管东生
“我们2000万起步,能把这个事情做成,就是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微导纳米总经理周仁对财经思享汇表示道。对初创公司来说,想要三五年就做成ALD设备这类“大”行业上游的设备公司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半导体领域的投资向来都是长周期、重投入的,如,ASML的新一代High NA光刻设备价值在3亿美元左右,苹果公司为了M3系列芯片的流片花费了约10亿美元,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建造晶圆厂的投资达到了400亿美元。
这也造成了全球半导体行业基本为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通常来说行业最顶尖的两到三家企业占据了各细分赛道大部分市场份额,这意味着只有体量足够大的企业才有能力进入半导体游戏的牌桌。
但如果回顾这些行业巨头的发迹历史,会发现这些企业的成长不仅离不开从0到1逐步壮大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创始人对企业方向的选择,以及紧紧抓住的时代机遇。微导纳米正是看准机会,踩准新能源行业的风口,接着继续涉足因AI火热正触底反弹的半导体行业,在国产替代的短暂窗口期极速狂飙,成就了国内ALD(原子层沉积,是一种先进的薄膜沉积工艺)设备领域的“隐形冠军”。
年轻的公司踩上了两个风口
2015年成立的微导纳米在半导体设备领域其实是一家极为年轻的公司。
在全球范围内,三大半导体设备巨头ASML、AMAT、LAM无不有数十年的历史,老大哥AMAT成立至今甚至已超过五十年,国内的头部半导体设备公司同样历史不短,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都在2000年之后的几年成立。

其实不少国内的知名半导体公司都是在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成立,这其中的背景便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首批出国的理工科留学生们,在海外半导体公司工作沉淀了技术和管理经验,“板凳要坐十年冷”之后,陆陆续续的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投身于半导体事业。
2015年同样也是中国半导体不可忽视的一年,在前一年的9月,规模达到千亿人民币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正式成立,寻找国内头部半导体公司,在不干扰公司日常管理的前提下进行股权投资,这可以看作是国资入场国内半导体行业的元年。
不仅是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半导体设备龙头,中芯国际、华虹、长电科技等在晶圆制造、先进封装的头部公司身上都能看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身影,到2019年大基金一期退出时,累计有七十余家半导体企业受益。
ALD本身就是半导体领域内先进的薄膜沉积技术,微导纳米是国内首家将其产业化应用于光伏领域的企业之一,于2015年底成立的微导纳米或许曾进入过大基金的视野,但由于ALD设备的特殊性,以及背后大股东在新能源行业的积累,微导纳米最初时常常被外界视为一家光伏领域的上游设备企业,但这和实际情况还有些偏差。
外界的误解:
光伏公司 OR 半导体公司?
随着ALD技术在半导体领域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以及微导纳米在28nm节点实现我国量产型High-k原子层沉积设备从无到有的突破,微导纳米在半导体领域声量大涨,更多人开始从半导体的角度来重估这家公司。
进军半导体,这确实是微导纳米最初的想法,微导纳米董事会秘书龙文在采访中曾表示:“微导纳米创立的初心是想把ALD(原子层沉积)、CVD(化学气相沉积)等半导体技术产业化应用,填补国内空白领域。公司未来要成为一家涉及多个行业的“技术平台型”公司”

但是反观2015年的国产半导体历史大背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要从零开始涉足如此宏大的行业,无论从资金端、客户导入端、国际巨头竞争端,难度可见一斑。为了存活下去,公司决定先从光伏行业切入,培育自身的“现金牛”业务,待时间成熟再回到老本行半导体行业。这一战略举措,取得重大的成功,使得公司不仅为光伏行业带来的先进的ALD技术,同时也为培养半导体业务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但也给外界认知公司带来了一些“疑惑”,单纯从财务数据或者炒股软件的分类上看,大多都简单认为公司是一家光伏公司,然后转型进军半导体。
其实,微导纳米的核心技术人员是以具备丰富经验的半导体人才为班底,包括副董事长、首席技术官黎微明和董事、副总经理李翔,两人均曾在ALD设备领军企业芬兰Picosun公司任职。其他两位分别是半导体事业部工艺副总监许所昌曾在中芯国际担任研发工程师,光伏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兴华,曾在中国台湾工研院、昱晶能源、泰州中来光电就职。
管理层方面,总经理周仁不仅有着泛林、科磊(KLA)海外半导体公司的工作经历,也有着国内数家头部半导体公司的工作经验,在多家中美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担任重要职位。
ALD设备确实有其特殊性。
首先,光伏制造和半导体制造都有薄膜沉积工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光伏其实也属于泛半导体行业,再者,像均匀性或者纯度之类的指标,光伏都要比半导体低很多,所以在技术壁垒上,半导体要比光伏高,以半导体ALD人才、设备进入光伏市场,也可以说是一种降维打击,通过ALD技术打开光伏薄膜沉积设备市场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实,除了上述原因外,ALD设备市场的晚熟是因其技术本身造成的。
姗姗来迟的ALD时代
提到半导体设备,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光刻机以及其背后的荷兰企业ASML,其实在整个晶圆制造设备过程中,光刻设备只是价值量最高的三大主要设备之一,占整个半导体设备市场的23%,另外两大设备则是刻蚀设备和薄膜沉积设备,占比分别在30%和25%,都要高于光刻设备市场。

此外,同属荷兰的薄膜沉积设备龙头ASM和ASML其实颇具渊源,在上个世纪80年代,ASM是极其罕见的同时拥有光刻、沉积、离子注入乃至封装设备的半导体公司,如今的光刻龙头ASML正是由ASM和飞利浦旗下光刻设备研发小组合并而来。
然而,伴随着半导体行业周期性的波动,ASM迫于公司财务报表,后来逐渐卖掉了包括ASML在内的离子注入(ASM Ion Implant)和芯片级封装(ASM Fico)等子公司。
压力下,断腕求生的ASM仅剩瞄准后端封装和贴片设备的ASM Pacific和专注在薄膜沉积设备的ASM International总部,彼时中国的半导体封装产业还未丰满,立足于亚太市场的ASM Pacific发展迅速,能稳定盈利,而总部的主营业务却因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AMAT等公司的加入而接连败退。
一直到2013年,ASM 在ALD领域十余年坚持不断的投入有了收获,以ALD为技术基底的High-K终于逐渐成为行业主流,ASM在半导体设备的前端业务终于开始扭亏为盈,ALD技术可以说挽救了ASM 。
ALD“晚熟”的原因其实恰恰是它的优势所在。
首先,引入一种反应物,使其发生化学吸附。一旦硅片表面达到饱和,剩余的反应物将被清除。接着,引入第二种反应物,与先前被吸附的物质发生反应。这样就可以在硅片表面形成一层原子级别的目标材料。通过重复这个过程,目标材料可以逐层生长,从而实现对材料厚度原子层级别的控制。
更为复杂精密的工艺流程,使得ALD涂层拥有良好的三维共形性,广泛适用于不同形状的基底;成膜大面积的均匀性,且致密、无针孔;可实现亚纳米级薄膜厚度的精确控制。但是,这同时也造成了相对于其他薄膜沉积技术,ALD技术的沉积速度相对较低,同时花费的成本更高。
这也是为何,早在 1974年,由芬兰的Tuomo Suntola博士就发明了ALD技术,可当时的半导体领域并没有什么公司愿意普及应用这项技术。
早期的芯片制造过程中,主要采用微米级的线宽要求,这种要求相对较低,可以满足大部分传统电子设备的需要。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芯片制造逐渐转向纳米级线宽,尤其是在2007年左右,芯片开始采用3D结构或深孔复杂结构。
这种转变使得芯片制造变得更加复杂和精密,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昂贵的设备,普通的PVD和CVD 沉积已逐渐难以满足晶圆厂商的需求,而ALD的优势恰好满足了芯片的这种“更复杂和精密”。
ASM能扭亏为盈,正是英特尔走到了45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需要把 ALD导入High-K Metal Gate(HKMG)工艺,这样,不管是Fin-FET还是Gate-All-Around(GAA),它的介质层采用ALD技术来做才能达到完全覆盖,也就是说想要生产制造7nm、5nm等先进制程,非 ALD不可。
从上世纪80年代ALD理论的发明,到先行者ASM十多年的苦苦支撑,再到下游晶圆厂逐渐开始生产先进制程芯片寻求超越摩尔定律的技术,ALD的时代终于来了,微导纳米的机会也来了。
微导纳米的“关键先生们”
周仁在谈到微导纳米大股东王燕清选择以ALD设备作为公司技术突破口时,仍忍不住称之为“神来之笔”,正如前文所说,光伏制造和半导体制造都有薄膜沉积工序,如果当时有一家公司能掌握ALD技术,确实能让企业突破单一行业的发展瓶颈,横跨光伏和半导体两大周期性行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企业的风险对冲。
喜欢钻研技术,在新能源领域摸爬滚打数十年,白手起家的“下海一代”王燕清比谁都清楚这是一步巧棋,但王燕清不是第一个尝试者,其实在微导纳米之前,最早一批研发推动ALD技术的企业ASM、Picosun等都有尝试在光伏领域应用该技术,但无一例外又陆续搁置了这一尝试。
简单来说就是,ALD技术虽然可行,但最大的难点在于ALD设备的成本并不占优势。更何况,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相比同时期的国外市场更加成熟,如何在有限的利润下将新ALD设备的应用成本降低,实现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这不仅是微导纳米成立之初要解决的问题,对下游光伏市场更小的国外ALD企业来说更是让人头痛的问题。
“天时是抓住禁运后半导体国产替代的窗口期,地利是无锡较为完善的地方技术产业链,人和是微导纳米有ALD领域的顶尖专家。”微导纳米总经理周仁对财经思享汇表示。
微导纳米首席技术官(CTO)及共同创始人黎微明,毫无疑问是“人”中的关键。1990年,这位只有22岁的年轻人,展现了他对学术和技术的热情与追求,选择离开家乡,远赴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攻读无机化学学位,后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许多国际知名企业,如ASM、Silecs、Picosun等从事ALD技术的应用与研发工作。
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黎微明在Picosun公司担任要职,负责ALD技术亚太区的运营和发展,他在这个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看到了ALD技术的巨大市场潜力。
到了2015年,黎微明辞去芬兰Picosun公司亚太区董事的职位,选择出任微导纳米的副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在这个新的舞台上,他负责该公司ALD技术路线和高端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他的归来,带回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来了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期望。
前有王燕清在新能源的铺路,后有ALD领域技术大拿的加盟,很快就有客户主动问起ALD设备应用在光伏领域的可能性。“第一个光伏ALD设备,其实是客户主动找过来的。有家企业想尝试采用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在最先进的光伏电池片里面,提升电池效率。”黎微明在采访中说道。
在接到需求后,微导纳米展现出了高效的研发能力,仅用半年时间就开发出了第一代样机。随后,黎微明带领设备和团队进驻客户工厂办公一年,不断调整工艺和技术,并针对性地改进产品和技术。2018年,微导纳米的光伏领域的“夸父”原子层沉积设备终于面世,这在业内激起了不小的水花。
黎微明在回忆这段历程时提到,当时微导纳米最缺乏的是时间的验证,国内公司对国产化设备及技术还持有怀疑态度。然而,事实上,他们的第一代产品在技术指标上已经远超当时能够买到的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
在如今的光伏领域,微导纳米已与国内前十的企业均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获得了通威股份、隆基股份、晶澳科技、阿特斯、天合光能等在内的多家知名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商的认可。

根据《中国光伏产业年度报告》(2020-2022)以及半导体设备行业上市公司公开信息,微导纳米近两年ALD产品收入规模已位于国内同类企业第一。在半导体领域,则实现了国产ALD设备在28nm集成电路制造关键工艺(高介电常数栅氧层材料沉积环节)中的突破。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在手订单 70.82 亿元(含 Demo 订单),其中,与 2022 年 1-9 月相比,光伏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244.32%,半导体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412.15%
“目前一年的短期目标,还是继续保持 ALD 领域的龙头位置,随着ALD及薄膜设备在各个领域逐步验证通过,中长期目标是争取五年内市值能持续突破。”周仁规划道。
END

发布于:北京
相关推荐
412.15%的半导体订单增长,是否意味着微导纳米的ALD时代来了
微导纳米三度IPO:公司增收不增利,前五大客户集中度过高
三星半导体死磕台积电:将放弃4纳米工艺直接过渡到3纳米
12月23日新股速递
日本半导体禁令,限制了啥?
张汝京看好的功率半导体,是否会有春天?
中国半导体制造的海外扩张之路
中国半导体产业如何加速国产化
半导体,要进入1nm以下时代了
中美关系缓和预期,半导体行业反转来了?
网址: 412.15%的半导体订单增长,是否意味着微导纳米的ALD时代来了 http://www.xishuta.com/newsview102694.html
推荐科技快讯

- 1问界商标转让释放信号:赛力斯 95792
- 2报告:抖音海外版下载量突破1 25736
- 3人类唯一的出路:变成人工智能 25175
- 4人类唯一的出路: 变成人工智 24611
- 5移动办公如何高效?谷歌研究了 24309
- 6华为 nova14深度评测: 13155
- 7滴滴出行被投诉价格操纵,网约 11888
- 82023年起,银行存取款迎来 10774
- 9五一来了,大数据杀熟又想来, 9794
- 10手机中存在一个监听开关,你关 9519